大丰收年
——家族传奇与时代风云的交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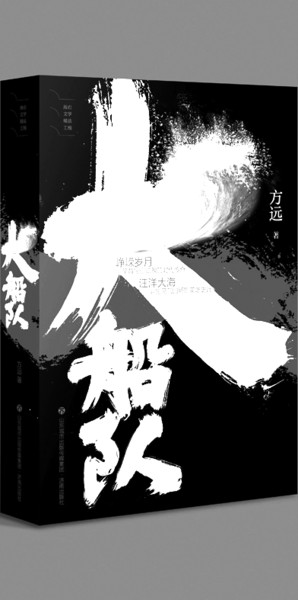
《大船队》作者:方远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好吧,天塌不下来的。”方英典微微一笑,“快去餐房吃两口饭,一会儿咱们去祠堂。”
去祠堂?潘士光知道,除了清明节及中元节等古老的祭奠日,平素里,宏德堂人很少去祠堂,除非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来到宏德堂十多年,潘士光先后侍候了方继先与方英典两代老爷,突然拜谒方氏祖先的次数屈指可数,他记忆犹新。那么现在,老爷方英典为什么要去祠堂?潘士光不由得心里一紧。
那是一个炎热的麦收季节,年仅十八岁的潘士光从平度县潘郭庄出发,肩背着一把锋利的镰刀,跟随同村的二十几个青壮年劳力,风雨兼程百余里,来到掖县地界,为大户人家收麦子。
这是潘士光第一次走出闭塞的家乡和一贫如洗的家,去年,为了给哥哥娶媳妇,爹娘拉下了一屁股饥荒。今年春天,凭着姐姐出嫁收的彩礼才基本填上了窟窿。潘士光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姐姐相当于被狠心的爹娘卖掉的,卖给了一户富裕人家的残疾儿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潘士光想,他一无所有,有的是力气,舍得下苦力就一定饿不死。他听村里的人说,到掖县给大户人家收麦子能挣钱,就主动跟着来了。
宏德堂有良田上百亩,村里村外都有,六七个长工负责庄稼的播种及日常管理,而到了收获的季节则要雇短工。
潘士光一行二十多人进了掖县地界,就开始受雇拔麦子,拔完了一家就继续北上,一直割到了方家村。
那天一早,宏德堂的老管家朱兆福站在村西口,翘首南望,等待着麦客。实际上,每年的麦客队伍都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割完麦子就约好明年再来,往往会失约。口头约定没有任何约束,就很少有人去遵守。
这年风调雨顺,是个多年不遇的大丰收年,沉甸甸的麦穗已经金黄,潘士光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此时此刻,老爷方继先正在丫鬟乔玉芬的侍奉下,站在村西的北地头上,看着麦浪滚滚,抑扬顿挫地背诵着白居易这首《观刈麦》。
二十多年前,老爹故去,方继先成为宏德堂的掌门人,他承袭家风,让宏德堂日渐兴盛。
去祠堂?潘士光知道,除了清明节及中元节等古老的祭奠日,平素里,宏德堂人很少去祠堂,除非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来到宏德堂十多年,潘士光先后侍候了方继先与方英典两代老爷,突然拜谒方氏祖先的次数屈指可数,他记忆犹新。那么现在,老爷方英典为什么要去祠堂?潘士光不由得心里一紧。
那是一个炎热的麦收季节,年仅十八岁的潘士光从平度县潘郭庄出发,肩背着一把锋利的镰刀,跟随同村的二十几个青壮年劳力,风雨兼程百余里,来到掖县地界,为大户人家收麦子。
这是潘士光第一次走出闭塞的家乡和一贫如洗的家,去年,为了给哥哥娶媳妇,爹娘拉下了一屁股饥荒。今年春天,凭着姐姐出嫁收的彩礼才基本填上了窟窿。潘士光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姐姐相当于被狠心的爹娘卖掉的,卖给了一户富裕人家的残疾儿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潘士光想,他一无所有,有的是力气,舍得下苦力就一定饿不死。他听村里的人说,到掖县给大户人家收麦子能挣钱,就主动跟着来了。
宏德堂有良田上百亩,村里村外都有,六七个长工负责庄稼的播种及日常管理,而到了收获的季节则要雇短工。
潘士光一行二十多人进了掖县地界,就开始受雇拔麦子,拔完了一家就继续北上,一直割到了方家村。
那天一早,宏德堂的老管家朱兆福站在村西口,翘首南望,等待着麦客。实际上,每年的麦客队伍都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割完麦子就约好明年再来,往往会失约。口头约定没有任何约束,就很少有人去遵守。
这年风调雨顺,是个多年不遇的大丰收年,沉甸甸的麦穗已经金黄,潘士光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此时此刻,老爷方继先正在丫鬟乔玉芬的侍奉下,站在村西的北地头上,看着麦浪滚滚,抑扬顿挫地背诵着白居易这首《观刈麦》。
二十多年前,老爹故去,方继先成为宏德堂的掌门人,他承袭家风,让宏德堂日渐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