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告别
——残酷而无意义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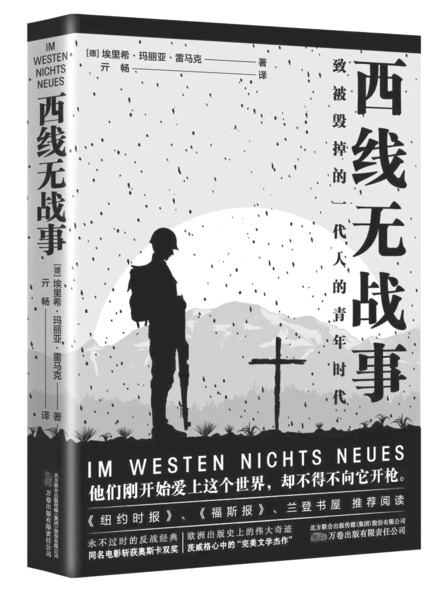
《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仔细观察他的每个表情,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想说些什么。真希望他能张开嘴大声喊出来啊!但他只是哭,头转向一边,什么都不说,也不提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这些已经离他远去了; 他现在正与他十九年短暂的生命独处,他哭,是因为它也要离开他了。
这是我见过的最无助、最艰难的告别。虽然蒂德詹的情况也很糟糕—这样一个壮汉尖叫着要找他的妈妈,怒目圆睁地拿着刀不让医生靠近,直到他倒下。
突然,凯梅里奇呻吟起来,喉咙里发出呼噜声。
我跳起来,踉跄地走出去,问:“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
当我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时,就紧紧地抓住他,“快点过来啊,否则弗朗茨·凯梅里奇会死的。”
他挣脱开来,问站在旁边的医护人员,“这是哪个病人?”他说:“二十六号床,腿被截肢了的那个。”
他骂骂咧咧地说:“我今天截了五条腿,怎么知道这是哪个。”他把我推开,跟旁边的医护人员说,“你去看看吧。”然后就跑去手术室了。
往病房走的时候,我愤怒地颤抖着。那人看着我说:“一个接一个的手术,从早上五点开始—老实告诉你,今天一天就有十六个人死掉了,你这是第十七个。今天肯定能有二十个。”
我身心俱疲,突然间什么也不能做了。我不想再骂人,因为这毫无意义;我想躺下,再也不起来了。
我们到凯梅里奇床边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的脸被泪水打湿,眼睛半睁着,像泛黄的老式牛角扣。
医护人员突然戳了我一下,“你要把他的东西带走吗?”我点了点头。
他继续说:“我们得马上抬走他,这张床还有用。病人们都已经躺到外面的走廊了。”我拿着东西,解下他的兵籍名牌。医护人员还要求提供士兵证。我告诉他,证件可能在文书室,然后就离开了。他们已经把弗朗茨拖到了一块帐篷布上,就在我身后。
门外的黑暗和微风让我松了口气。我拼命地呼吸,风吹在脸上,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情和柔软; 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漂亮的姑娘、开花的草地和白色的云朵。我迈着大步,越走越快,然后跑了起来。士兵们从我身边经过,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却让我不安。大地充斥着力量,通过脚底涌向身体。夜晚充斥着噼啪的枪声,前线炮火如同一首协奏曲。
这是我见过的最无助、最艰难的告别。虽然蒂德詹的情况也很糟糕—这样一个壮汉尖叫着要找他的妈妈,怒目圆睁地拿着刀不让医生靠近,直到他倒下。
突然,凯梅里奇呻吟起来,喉咙里发出呼噜声。
我跳起来,踉跄地走出去,问:“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
当我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时,就紧紧地抓住他,“快点过来啊,否则弗朗茨·凯梅里奇会死的。”
他挣脱开来,问站在旁边的医护人员,“这是哪个病人?”他说:“二十六号床,腿被截肢了的那个。”
他骂骂咧咧地说:“我今天截了五条腿,怎么知道这是哪个。”他把我推开,跟旁边的医护人员说,“你去看看吧。”然后就跑去手术室了。
往病房走的时候,我愤怒地颤抖着。那人看着我说:“一个接一个的手术,从早上五点开始—老实告诉你,今天一天就有十六个人死掉了,你这是第十七个。今天肯定能有二十个。”
我身心俱疲,突然间什么也不能做了。我不想再骂人,因为这毫无意义;我想躺下,再也不起来了。
我们到凯梅里奇床边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的脸被泪水打湿,眼睛半睁着,像泛黄的老式牛角扣。
医护人员突然戳了我一下,“你要把他的东西带走吗?”我点了点头。
他继续说:“我们得马上抬走他,这张床还有用。病人们都已经躺到外面的走廊了。”我拿着东西,解下他的兵籍名牌。医护人员还要求提供士兵证。我告诉他,证件可能在文书室,然后就离开了。他们已经把弗朗茨拖到了一块帐篷布上,就在我身后。
门外的黑暗和微风让我松了口气。我拼命地呼吸,风吹在脸上,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情和柔软; 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漂亮的姑娘、开花的草地和白色的云朵。我迈着大步,越走越快,然后跑了起来。士兵们从我身边经过,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却让我不安。大地充斥着力量,通过脚底涌向身体。夜晚充斥着噼啪的枪声,前线炮火如同一首协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