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爱与执”
非虚构散文集《执念》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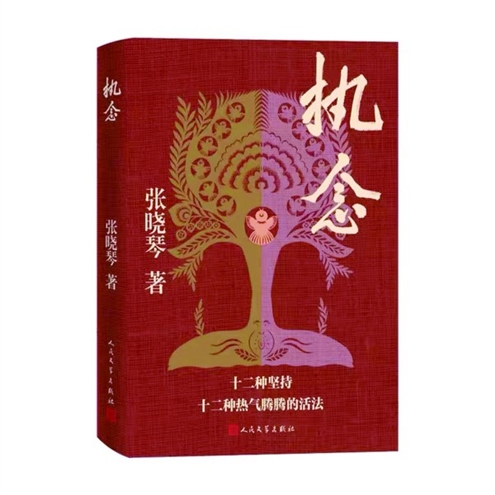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日前,非虚构散文集《执念》正式出版,作家张晓琴历时两年深入甘肃,足迹遍布河西走廊、莲花山、拉卜楞寺,用写作记录了西北大地上非遗传承的人和事,讲述着普通人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真心。而在技艺传承的背后,书中详细描绘了技艺与时间的对抗,以及一场事关人本身的执着与热望。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见习记者 梁柏林
“执念”就是对“细”的呈现
《执念》的创作缘起于一次远行,作者张晓琴偶然结识了唢呐传承人马自刚。张晓琴在与他的交谈中发现,马自刚并不认为自己过着电影《百鸟朝凤》中所讲述的悲情人生。马自刚一句“我们的命运没有那么悲惨”,以及“不一样”这三个字,深深触动了她。
“不一样”,恰恰就应该是文学开始的地方。于是,她踏上了寻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旅程,十二位传承人的故事,走出了《执念》这本书。相比于对非遗本身的关注,《执念》更加关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生活状态。谈及创作《执念》的过程,张晓琴感慨万千。
“我从一百多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选了十二个不同传承领域、不同年龄段的代表,最大的是‘50后’,最小的是‘90后’,开始了我的访谈路程。”据了解,为了完成这些访谈,作者前后行走了四千多公里,“坐过飞机,也坐过羊皮筏子,有过差点出车祸的经历,有的地方吃不到饭,有的地方手机没信号,但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特别宝贵的一笔财富。”
在不断追求短平快的当下,始终有一些人长期专注甚至近乎孤独地钻研某一门技艺,针对这些人,张晓琴借用了《执念》中的人物许明堂说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认识:细的东西是精良,粗的东西是灭亡,我喜欢细的东西,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张晓琴看来,执念就是对“细”的呈现,执念的本质是“不妥协的专注”,而“细”正是对“妥协”的拒绝。这些传承人认准了一门手艺,就执着地做下去,不管遇到多少困难,这份心劲儿没丢,这就是执念。每个传承人都有各自热爱的技艺,相同的执念藏在每个人的心里,以不同的形态生长,让日子聚起生生不息的热气。“只要有执念,有热爱,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
源于热爱,终于坚守
“书中不仅写了十二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还写了这些有执念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本书除了有文学价值,还有史料的价值。”刘震云如此评价《执念》。他认为,张晓琴写的不仅仅是十二项非遗,更是这些传承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内核。书中记录的十二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各有各的行当,各有各的不容易,尤其如今传承方式也有所改变——子女跟随父母传承非遗的情况比较少,基本上都是有些“执念”的人过来当徒弟。
而“执念”,在刘震云看来就是“喜欢”。
“晓琴的《执念》我读了两遍,她在这本书里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喜欢。喜欢,是做一件事最主要的动力。”源于心底的纯粹而炽热的喜欢,足以形成对一事一物全身心投入的“疯魔”状态,只有追求极致,全身心投入,才能突破自我、实现升华。“一般的文学作品写的是故事,比这稍微好一点的写的是人物,其实更重要的是故事和人物背后的道理,看似写的是这个,其实是写这背后的道理。”
张晓琴在非遗的背后看到了“执念”,在“执念”背后看见了每一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热爱。《执念》写出了这样一种道理:“执念”是喜欢,是企图心,是“不疯魔不成佛”,是“要走不一样的路,既不同于他人,也有别于自己过去的路子”。
而在水均益看来,所谓的执念或许还是一种“一根筋”,一种“沉默和壮阔的对抗”。
“和什么对抗?和时间,和世俗,甚至是要改变命运的一种对抗。”《执念》中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一股劲儿”就是最为形象的体现,他们热爱自己的手艺,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执念支撑着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把手艺传承下去。在书中,张晓琴让这些濒临消失的文化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也让人们看到执念的力量——它既是壮阔的对抗,也成就朴素的生活。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见习记者 梁柏林
“执念”就是对“细”的呈现
《执念》的创作缘起于一次远行,作者张晓琴偶然结识了唢呐传承人马自刚。张晓琴在与他的交谈中发现,马自刚并不认为自己过着电影《百鸟朝凤》中所讲述的悲情人生。马自刚一句“我们的命运没有那么悲惨”,以及“不一样”这三个字,深深触动了她。
“不一样”,恰恰就应该是文学开始的地方。于是,她踏上了寻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旅程,十二位传承人的故事,走出了《执念》这本书。相比于对非遗本身的关注,《执念》更加关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生活状态。谈及创作《执念》的过程,张晓琴感慨万千。
“我从一百多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选了十二个不同传承领域、不同年龄段的代表,最大的是‘50后’,最小的是‘90后’,开始了我的访谈路程。”据了解,为了完成这些访谈,作者前后行走了四千多公里,“坐过飞机,也坐过羊皮筏子,有过差点出车祸的经历,有的地方吃不到饭,有的地方手机没信号,但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特别宝贵的一笔财富。”
在不断追求短平快的当下,始终有一些人长期专注甚至近乎孤独地钻研某一门技艺,针对这些人,张晓琴借用了《执念》中的人物许明堂说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认识:细的东西是精良,粗的东西是灭亡,我喜欢细的东西,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张晓琴看来,执念就是对“细”的呈现,执念的本质是“不妥协的专注”,而“细”正是对“妥协”的拒绝。这些传承人认准了一门手艺,就执着地做下去,不管遇到多少困难,这份心劲儿没丢,这就是执念。每个传承人都有各自热爱的技艺,相同的执念藏在每个人的心里,以不同的形态生长,让日子聚起生生不息的热气。“只要有执念,有热爱,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
源于热爱,终于坚守
“书中不仅写了十二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还写了这些有执念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本书除了有文学价值,还有史料的价值。”刘震云如此评价《执念》。他认为,张晓琴写的不仅仅是十二项非遗,更是这些传承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内核。书中记录的十二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各有各的行当,各有各的不容易,尤其如今传承方式也有所改变——子女跟随父母传承非遗的情况比较少,基本上都是有些“执念”的人过来当徒弟。
而“执念”,在刘震云看来就是“喜欢”。
“晓琴的《执念》我读了两遍,她在这本书里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喜欢。喜欢,是做一件事最主要的动力。”源于心底的纯粹而炽热的喜欢,足以形成对一事一物全身心投入的“疯魔”状态,只有追求极致,全身心投入,才能突破自我、实现升华。“一般的文学作品写的是故事,比这稍微好一点的写的是人物,其实更重要的是故事和人物背后的道理,看似写的是这个,其实是写这背后的道理。”
张晓琴在非遗的背后看到了“执念”,在“执念”背后看见了每一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热爱。《执念》写出了这样一种道理:“执念”是喜欢,是企图心,是“不疯魔不成佛”,是“要走不一样的路,既不同于他人,也有别于自己过去的路子”。
而在水均益看来,所谓的执念或许还是一种“一根筋”,一种“沉默和壮阔的对抗”。
“和什么对抗?和时间,和世俗,甚至是要改变命运的一种对抗。”《执念》中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一股劲儿”就是最为形象的体现,他们热爱自己的手艺,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执念支撑着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把手艺传承下去。在书中,张晓琴让这些濒临消失的文化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也让人们看到执念的力量——它既是壮阔的对抗,也成就朴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