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契
——书写青藏高原的“山乡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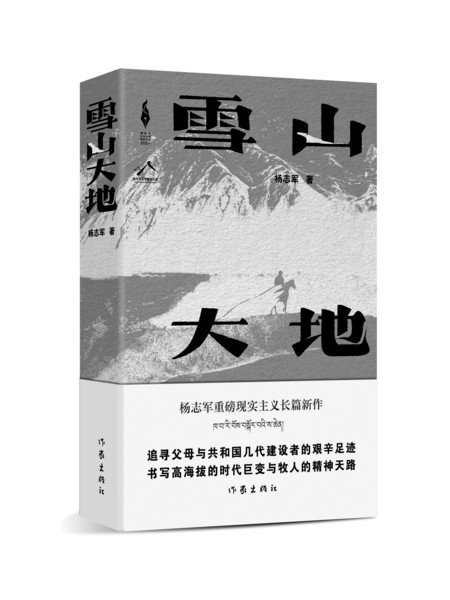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父亲问:“你是不是也应该用歌声回答他?”梅朵说:“噢呀。”然后就唱起来:
群山里的高峰,众马里的骏马,
我家的哥哥,草原上的好汉,
人堆里的尖子,人人喜欢的赛马王。
父亲问:“真正的骏马你见过没有?”梅朵摇头。“走走走,我领你去看。”他拉着梅朵的手,来到帐房外面,走向了在草滩上吃草的日尕。
日尕看到主人,立刻仰头摆出一副目视远方的姿势,然后移动眼球,鼻孔一掀一掀地闻了闻梅朵的气味。
父亲说:“这么灵性的马没见过吧?它知道你要骑它。”说着抱起梅朵放在了卸去鞍鞯的马背上。平阔的马背让梅朵无法叉开两腿骑着,她跪了一会儿,看马背纹丝不动,便站了起来。
日尕朝前走去,没有一点起伏,梅朵站在马背上,也没有一点摇晃。父亲欣赏地看着:“梅朵天生是个好骑手,再长一长,就可以骑着日尕参加赛马会啦。”日尕走出去不远又走回父亲身边。
父亲要抱梅朵下来,她却拽着鬃毛趴在了马脖子上。日尕立刻低头,梅朵跳到了地上。父亲说:“你们好像商量好啦。”说着摸了一下日尕,让它继续去吃草,自己拉着梅朵,走过去盘腿坐在了草地上梅朵红的身边。
梅朵红一身赤炭似的长毛,卧在那里就像堆了一大堆牛粪火。它看都不看父亲一眼,耷拉着厚重的耳朵,把三角眼藏在毛后面,一眨一眨地盯着前面。
它不理父亲是因为父亲在家里住过,在它的意识里住过的人就是家里人,对家里人有什么必要盯住不放呢?它需要盯紧的是开会的人,那些人它大都没见过。在它貌似漫不经心的盯视中,警惕和威慑会像风一样传给那些懂得藏獒的牧人。
桑杰和卓玛还有央金提着铜壶端着糌粑匣子朝父亲走来。父亲赶紧从上衣口袋掏出碗来:“轮到我了吗?谢谢啦。”卓玛倒茶,桑杰捧茶,央金放下了糌粑匣子。
卓玛问:“强巴县长啦,下边有没有草原和牧场?”“下边没有草原,下边有田地,种的是庄稼。”“怪不得下边人要吃沁多的牛羊肉。”央金跑向不远处的溪流,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鱼。梅朵跟了过去。
卓玛要去帐房继续烧茶,有礼貌地说:“强巴县长啦,你慢慢吃慢慢喝。”父亲说:“多谢啦。”桑杰弯着腰小心翼翼地问:“强巴县长啦,才让可好?”“我正要告诉你呢,阿尼琼贡的曼巴治不好才让的聋哑,我把他送到西宁去啦。西宁有我的家,家里人会照顾他,请你一万个放心。”
群山里的高峰,众马里的骏马,
我家的哥哥,草原上的好汉,
人堆里的尖子,人人喜欢的赛马王。
父亲问:“真正的骏马你见过没有?”梅朵摇头。“走走走,我领你去看。”他拉着梅朵的手,来到帐房外面,走向了在草滩上吃草的日尕。
日尕看到主人,立刻仰头摆出一副目视远方的姿势,然后移动眼球,鼻孔一掀一掀地闻了闻梅朵的气味。
父亲说:“这么灵性的马没见过吧?它知道你要骑它。”说着抱起梅朵放在了卸去鞍鞯的马背上。平阔的马背让梅朵无法叉开两腿骑着,她跪了一会儿,看马背纹丝不动,便站了起来。
日尕朝前走去,没有一点起伏,梅朵站在马背上,也没有一点摇晃。父亲欣赏地看着:“梅朵天生是个好骑手,再长一长,就可以骑着日尕参加赛马会啦。”日尕走出去不远又走回父亲身边。
父亲要抱梅朵下来,她却拽着鬃毛趴在了马脖子上。日尕立刻低头,梅朵跳到了地上。父亲说:“你们好像商量好啦。”说着摸了一下日尕,让它继续去吃草,自己拉着梅朵,走过去盘腿坐在了草地上梅朵红的身边。
梅朵红一身赤炭似的长毛,卧在那里就像堆了一大堆牛粪火。它看都不看父亲一眼,耷拉着厚重的耳朵,把三角眼藏在毛后面,一眨一眨地盯着前面。
它不理父亲是因为父亲在家里住过,在它的意识里住过的人就是家里人,对家里人有什么必要盯住不放呢?它需要盯紧的是开会的人,那些人它大都没见过。在它貌似漫不经心的盯视中,警惕和威慑会像风一样传给那些懂得藏獒的牧人。
桑杰和卓玛还有央金提着铜壶端着糌粑匣子朝父亲走来。父亲赶紧从上衣口袋掏出碗来:“轮到我了吗?谢谢啦。”卓玛倒茶,桑杰捧茶,央金放下了糌粑匣子。
卓玛问:“强巴县长啦,下边有没有草原和牧场?”“下边没有草原,下边有田地,种的是庄稼。”“怪不得下边人要吃沁多的牛羊肉。”央金跑向不远处的溪流,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鱼。梅朵跟了过去。
卓玛要去帐房继续烧茶,有礼貌地说:“强巴县长啦,你慢慢吃慢慢喝。”父亲说:“多谢啦。”桑杰弯着腰小心翼翼地问:“强巴县长啦,才让可好?”“我正要告诉你呢,阿尼琼贡的曼巴治不好才让的聋哑,我把他送到西宁去啦。西宁有我的家,家里人会照顾他,请你一万个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