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
——书写青藏高原的“山乡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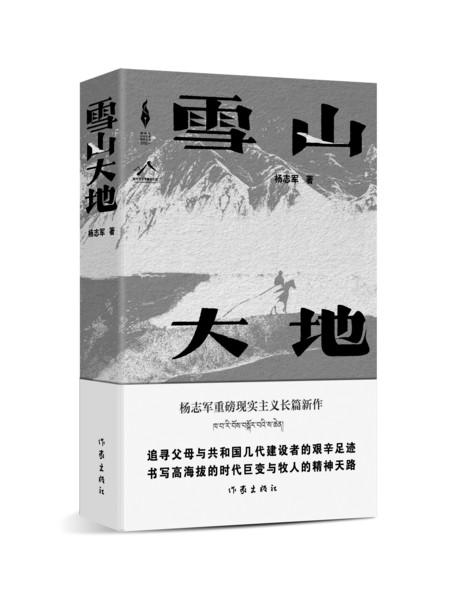
《雪山大地》作者:杨志军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于是,每当晚霞燃烧,我会立在巷口,朝街尽头张望,有时牵着两只羊,有时就我自己,孤零零地伫立着。在没有才让的日子里,我发现我是多么孤独啊,甚至有些凄凉。
后来姥爷来了,再后来姥姥也来了,我们三个人会站在巷口,一直望到太阳落山,望到天色麻黑。母亲和才让回来的时候是半夜,姥爷听到有人敲院门,说一声“回来了”,爬起来就去开门。
进了家,姥姥问:“肚子吃了没?”姥爷问:“治好了没?”我望着才让笑,才让也冲我笑。突然他扑过来,抱住我,用他的额头碰了一下我的额头。
风从祈福真言的石堆上流过,
从哈达覆盖的雪山大地上流过,
从人心的蓝白红绿黄上流过,
风唱着扎西德勒从爱的空间流过。
草原疯狂地延伸着,用辽阔嘲笑着马蹄,似乎马永远走不出草原,马终究会累死在它的辽阔里。马蹄也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嘲笑着草原,似乎草原是不够踩踏的,踏着踏着就会踏没了。
前往沁多公社的父亲路过“一间房”,来到前些日子到过的那片草原,看到了那座白色方塔和那座旗幡猎猎的祈福真言石经堆,却没看到角巴家的大帐房,只有扎营的痕迹固执地定位在草原上,就像残留的梦,依稀闪现着过往的日子。
他前后左右转转,凭常识走向了有山的地方,这个时节的牧人大都在山上,在夏窝子里。他走过了一山又一山,看到牧草都是断了头的,黑土连片起伏,说明牛羊不久前采食过这里。
可是现在呢,牧人和牲畜去了哪里?黄昏不期而至,彤云密布的西天如同新添了牛粪的火炉,草原在凄艳中静谧到死去。
他正在疑惑,心说要不要原路返回,就见远处狼烟冒起,直直地如同顶天的柱子。他打马跑去,忽听一声枪响,又一声枪响。日尕戛然止步,本能地后退了几步。
父亲双腿一夹说:“过去,看看是谁在打枪。”日尕看主人不怕,自己也就释然了,因为在它闻到的气息里此时并不存在什么危险。它和山风一起吹过一道缓慢的山梁,直奔高旷的风毛菊连片成海的草场。
角巴在那里,许多牧人都在那里。父亲跳下马背的同时,随手把缰绳一丢。日尕吃草去了,对它来说抓紧时间补充能量比什么都重要。父亲大步走向角巴。
角巴说:“强巴县长啦,是多嘴多舌的百灵鸟把话传到你耳朵里了吗?你来得不是时候,糌粑吃不上,酥油茶没的喝。”父亲没好气地说:“你把公家人看成什么啦,酒囊饭袋吗,整天跑来跑去就为了吃喝?”
后来姥爷来了,再后来姥姥也来了,我们三个人会站在巷口,一直望到太阳落山,望到天色麻黑。母亲和才让回来的时候是半夜,姥爷听到有人敲院门,说一声“回来了”,爬起来就去开门。
进了家,姥姥问:“肚子吃了没?”姥爷问:“治好了没?”我望着才让笑,才让也冲我笑。突然他扑过来,抱住我,用他的额头碰了一下我的额头。
风从祈福真言的石堆上流过,
从哈达覆盖的雪山大地上流过,
从人心的蓝白红绿黄上流过,
风唱着扎西德勒从爱的空间流过。
草原疯狂地延伸着,用辽阔嘲笑着马蹄,似乎马永远走不出草原,马终究会累死在它的辽阔里。马蹄也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嘲笑着草原,似乎草原是不够踩踏的,踏着踏着就会踏没了。
前往沁多公社的父亲路过“一间房”,来到前些日子到过的那片草原,看到了那座白色方塔和那座旗幡猎猎的祈福真言石经堆,却没看到角巴家的大帐房,只有扎营的痕迹固执地定位在草原上,就像残留的梦,依稀闪现着过往的日子。
他前后左右转转,凭常识走向了有山的地方,这个时节的牧人大都在山上,在夏窝子里。他走过了一山又一山,看到牧草都是断了头的,黑土连片起伏,说明牛羊不久前采食过这里。
可是现在呢,牧人和牲畜去了哪里?黄昏不期而至,彤云密布的西天如同新添了牛粪的火炉,草原在凄艳中静谧到死去。
他正在疑惑,心说要不要原路返回,就见远处狼烟冒起,直直地如同顶天的柱子。他打马跑去,忽听一声枪响,又一声枪响。日尕戛然止步,本能地后退了几步。
父亲双腿一夹说:“过去,看看是谁在打枪。”日尕看主人不怕,自己也就释然了,因为在它闻到的气息里此时并不存在什么危险。它和山风一起吹过一道缓慢的山梁,直奔高旷的风毛菊连片成海的草场。
角巴在那里,许多牧人都在那里。父亲跳下马背的同时,随手把缰绳一丢。日尕吃草去了,对它来说抓紧时间补充能量比什么都重要。父亲大步走向角巴。
角巴说:“强巴县长啦,是多嘴多舌的百灵鸟把话传到你耳朵里了吗?你来得不是时候,糌粑吃不上,酥油茶没的喝。”父亲没好气地说:“你把公家人看成什么啦,酒囊饭袋吗,整天跑来跑去就为了吃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