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羊
——书写青藏高原的“山乡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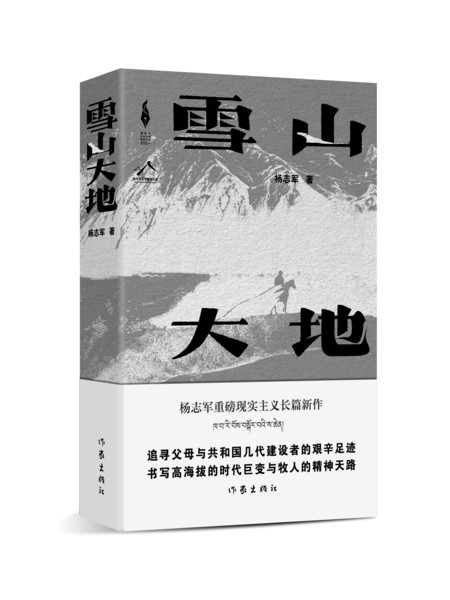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要是有回信或者有什么东西带给强巴副县长,他明天上午来取。又叮嘱道:“才让就留下啦,他今天就吃了拇指大的一块馒头,姐姐摸摸肚子就知道啦。”在果果拉马离开时,才让下意识地跟了过去。
母亲上前牵住他的手,对我说:“不知道你们两个谁大,看上去差不多。”我凑过去想跟他比个子。他吃惊得后退着,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一阵风吹来,我的鼻子里顿时灌满了浓浓的酥油味。
这是一个星期天,已经下午了。斜射的阳光把小巷分割成了阴阳两半,风也是一边凉一边热。才让走在阳光里,望着两边高高的土墙和前面深深的门洞,好几次都想停下来。
母亲牢牢攥着他的手说:“你第一次来西宁吧?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后来才让告诉我,他当时忐忑极了,就像一只小羊闯进了陌生的羊群。不不,他比小羊更不幸,小羊在陌生的羊群里会高声咩叫着寻找母羊和熟悉的伴侣,他却只能一声不吭,连表示一下疑惑都不可能。他来自草原,对城市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抵触,所有迎面而来的,对他都是无法判断优劣好坏的巨大未知。我们进了院门,又进了我家居住的南房。姥姥惊讶得叫了一声:“这是谁家的娃娃,你怎么领进来了?”姥爷说:“别紧张,人家又不是来吃来喝的。”母亲说:“不吃不喝来家里干什么?”姥爷姥姥包括我都愣住了。
这是1959年的下半年,渐渐凸显的饥荒让谁也无法轻松面对家中来客这件事,连不到五岁的我都本能地有了沉甸甸的压力。大人们都说我聪明,聪明在这个时候让我朦朦胧胧意识到:本来就吃不饱的食物又要从我们嘴里扒拉出去一些了。
母亲又说:“他阿妈死了,洋洋他爸也差一点死掉。”然后拿着信念起来,还没念完,姥姥就哭了。她是一个谁死都会哭的人,何况是一个救了父亲命的人。
她捯动着小脚过去,一手抱住才让的头,一手摸着他的光脊梁:“没娘的娃娃太孽障(可怜),大夏天还穿着皮袍,光身子上连个衬衣也没有。”说着又哭。母亲也抹起了眼泪。
姥爷长叹一声说:“这是恩人的娃娃,我们不能对不起。”我那时还不理解父亲信中的话,也不理解大人们的眼泪,只觉得家里来了一个小藏族人,他已经没有阿妈了。
我警惕地想:是不是他没有了阿妈,就来这里找阿妈?这里的阿妈是我的阿妈。才让一看姥姥摸他的光脊梁,就懂事地把堆在腰里的皮袍提起来穿在了身上,而且像汉族人一样两只胳膊都套进了袖子。
母亲上前牵住他的手,对我说:“不知道你们两个谁大,看上去差不多。”我凑过去想跟他比个子。他吃惊得后退着,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一阵风吹来,我的鼻子里顿时灌满了浓浓的酥油味。
这是一个星期天,已经下午了。斜射的阳光把小巷分割成了阴阳两半,风也是一边凉一边热。才让走在阳光里,望着两边高高的土墙和前面深深的门洞,好几次都想停下来。
母亲牢牢攥着他的手说:“你第一次来西宁吧?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后来才让告诉我,他当时忐忑极了,就像一只小羊闯进了陌生的羊群。不不,他比小羊更不幸,小羊在陌生的羊群里会高声咩叫着寻找母羊和熟悉的伴侣,他却只能一声不吭,连表示一下疑惑都不可能。他来自草原,对城市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抵触,所有迎面而来的,对他都是无法判断优劣好坏的巨大未知。我们进了院门,又进了我家居住的南房。姥姥惊讶得叫了一声:“这是谁家的娃娃,你怎么领进来了?”姥爷说:“别紧张,人家又不是来吃来喝的。”母亲说:“不吃不喝来家里干什么?”姥爷姥姥包括我都愣住了。
这是1959年的下半年,渐渐凸显的饥荒让谁也无法轻松面对家中来客这件事,连不到五岁的我都本能地有了沉甸甸的压力。大人们都说我聪明,聪明在这个时候让我朦朦胧胧意识到:本来就吃不饱的食物又要从我们嘴里扒拉出去一些了。
母亲又说:“他阿妈死了,洋洋他爸也差一点死掉。”然后拿着信念起来,还没念完,姥姥就哭了。她是一个谁死都会哭的人,何况是一个救了父亲命的人。
她捯动着小脚过去,一手抱住才让的头,一手摸着他的光脊梁:“没娘的娃娃太孽障(可怜),大夏天还穿着皮袍,光身子上连个衬衣也没有。”说着又哭。母亲也抹起了眼泪。
姥爷长叹一声说:“这是恩人的娃娃,我们不能对不起。”我那时还不理解父亲信中的话,也不理解大人们的眼泪,只觉得家里来了一个小藏族人,他已经没有阿妈了。
我警惕地想:是不是他没有了阿妈,就来这里找阿妈?这里的阿妈是我的阿妈。才让一看姥姥摸他的光脊梁,就懂事地把堆在腰里的皮袍提起来穿在了身上,而且像汉族人一样两只胳膊都套进了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