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哪吒谈封神 看懂中国神话
《出仙入凡说封神》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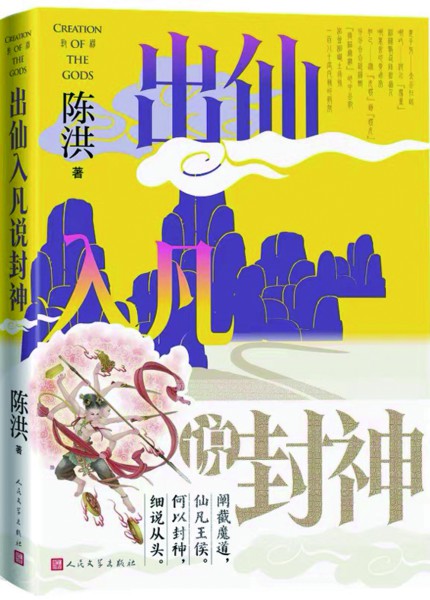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今春以来,《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现象级热映影片,作为家喻户晓的神话“IP”,电影主角哪吒得到描写最详细完整的著作非《封神演义》莫属。日前,“南开讲席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陈洪新著《出仙入凡说封神》出版,该书以严谨、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揭示了《封神演义》深层而有趣的内蕴。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实习生 张渊栋
“一流半”小说的“超一流”影响力
阐、截二派相争,商、周两朝对垒,四股势力交织对抗,又与姜子牙封神故事与武王伐纣历史融合,在一个个错落有致又跌宕起伏的情节中,由绚烂想象力构成的神话世界就此诞生。古典神魔小说代表作《封神演义》,以其通俗的语言描写与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百姓津津乐道,成为了文学界长盛不衰的佳作,其中诸多人物形象更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其实《封神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是一流小说,仅位于一流半到二流之间,所以,无论是四大名著还是所谓的六大名著,《封神演义》都未曾上榜。”谈到《封神演义》在历史上的地位,作者陈洪表示,就是这样一本小说,在民间却有着与《西游记》不相上下的影响力,不仅对中国的文化生态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成为了中国人思想观念与想象力重要来源。
通读全书,《封神演义》情节的一大特点是把人间的改朝换代与仙界正邪之争交织到一起,叙事有时着眼于人间、人事,如“黄飞虎反五关”,像极了《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忽而又来到神魔之中,各类法术与法宝层出不穷。“这种结构与希腊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处,套用一个思想史的术语,就是‘联地天通’。”陈洪解释道。经由这种时空的转换,读者的眼界和思想也将随之一同变得开阔,宏大场景与峰回路转背后,是在另一视角下对人生百态的体察与展现。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封神演义》学术研究的一些问题,本书同样有着诸多探讨。如作者究竟是何人,《封神演义》与《西游记》的关系孰先孰后?对这些问题的一一铺展也将成为挖掘书中文化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无论是当代的普通人还是明朝的普通人,他们的关注点、他们心中的知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在何处,这是我们从《封神演义》中可以去关注和研究的东西。”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昊苏认为,阅读本书,不仅是回味小说中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体味作者是如何一步步虚构并建立一个世界,而它又是如何一步步被普罗大众与普通读者接受的。
探索哪吒形象“神魔”之变
2025年开年,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强势崛起,截至目前,该电影全球总票房突破146亿元,位列全球影史第七,更成为中国影史首部观影人次破3亿电影。不仅在数据上频频刷新纪录,经由电影的传播,一个经典的“魔童”哪吒形象也自此深深印刻在全球观众心中。哪吒为“魔”是天生如此还是艺术创造,在本书中,作者就此开设“单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解读。
陈洪表示,电影中的“魔童哪吒”形象,以及哪吒与敖丙“双胞胎”的情节核心是作者巧妙嫁接出的成果。“这种嫁接的近缘母本自然是《封神演义》,而若追寻基因谱系,则是自唐至明千年间,中外文化、雅俗文化交融所‘定型’的哪吒,虚与实、历史与文化的不断交织使得这一形象本身就带有潜在而又强烈的‘魔性’。”
记者了解到,哪吒从读音、形象到其概念的生成均与文化交融沟通密不可分。“哪吒在早期经文中其实是咒语里的一个发音。”陈洪表示,到唐朝时,一个名为“哪吒”的人格形象才从经文中确立出来,一直到晚唐,才有了关于哪吒的故事。宋朝时,哪吒的故事复杂起来了,其与父亲的关系,以及他“莲花化身”的身份也是在那时以传说的形式出现。于是在《封神演义》中,哪吒还骨肉给父母、莲花化身的故事便已然相当生动。“可以说,原著小说里的哪吒兼具善恶两性,善是主要的,但是也有恶作剧的一面,这是影片得以进行改编的基因。”
假如历史与小说均是“魔童”哪吒的嫁接母本,那么其“接穗”或许是来自于众多已然取得成功的小说、剧本,尤其是小说《绝代双骄》中的小“魔头”江小鱼。“魔童的设定,是把古龙武侠小说《绝代双骄》江小鱼与花无缺的部分情节,嫁接到哪吒与敖丙身上,促成了此次成功的改编。”陈洪表示,电影中哪吒的性格与命运与江小鱼等人物存在大量的相似因子,并进一步为类似形象注入了新的生命,这种“借势”在动画电影中取得了相当有意义的成功。
殷郊的“莎士比亚式”悲剧
从正义化身、帝师典范的姜子牙,到暴君代表、荒淫无道的商纣王,再到“妖女”苏妲己、散仙陆压、猛将黄飞虎,《封神演义》中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学形象,他们最终都破蛹化蝶,成为家喻户晓的角色。而在其中,近期得到广泛热议的殷郊同样具有深刻且复杂的文学性。据陈洪表示,殷郊的形象在《封神演义》里涉及的内容不太多,但在《封神演义》之前的《武王伐纣平话》中则承担了极为重要的戏份。
陈洪表示,在这本书中,殷郊被塑造成复仇者的形象,其父亲纣王因为宠幸妲己,残忍杀害了他的母亲,又听信妲己的话要杀他。若要给母亲报仇就要杀父亲,这就是一种伦理上的困境。而若要战胜父亲,则只能去投靠父母之邦的敌国,他要投降到敌人的阵营中,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正义。在进退与向背的犹豫和反复之间,不仅丧失了性命,还背负上了背信弃义的罪名。
“最后,在《武王伐纣平话》故事中,殷郊选择亲手杀死了纣王与妲己。”陈洪表示,这种内心的斗争和在矛盾面前的选择,很有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感觉,不是一般是非得失的问题,是内心的人格的挣扎。这种复杂的性格让人物变得丰满,也成为了小说中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形象之一。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实习生 张渊栋
“一流半”小说的“超一流”影响力
阐、截二派相争,商、周两朝对垒,四股势力交织对抗,又与姜子牙封神故事与武王伐纣历史融合,在一个个错落有致又跌宕起伏的情节中,由绚烂想象力构成的神话世界就此诞生。古典神魔小说代表作《封神演义》,以其通俗的语言描写与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百姓津津乐道,成为了文学界长盛不衰的佳作,其中诸多人物形象更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其实《封神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是一流小说,仅位于一流半到二流之间,所以,无论是四大名著还是所谓的六大名著,《封神演义》都未曾上榜。”谈到《封神演义》在历史上的地位,作者陈洪表示,就是这样一本小说,在民间却有着与《西游记》不相上下的影响力,不仅对中国的文化生态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成为了中国人思想观念与想象力重要来源。
通读全书,《封神演义》情节的一大特点是把人间的改朝换代与仙界正邪之争交织到一起,叙事有时着眼于人间、人事,如“黄飞虎反五关”,像极了《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忽而又来到神魔之中,各类法术与法宝层出不穷。“这种结构与希腊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处,套用一个思想史的术语,就是‘联地天通’。”陈洪解释道。经由这种时空的转换,读者的眼界和思想也将随之一同变得开阔,宏大场景与峰回路转背后,是在另一视角下对人生百态的体察与展现。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封神演义》学术研究的一些问题,本书同样有着诸多探讨。如作者究竟是何人,《封神演义》与《西游记》的关系孰先孰后?对这些问题的一一铺展也将成为挖掘书中文化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无论是当代的普通人还是明朝的普通人,他们的关注点、他们心中的知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在何处,这是我们从《封神演义》中可以去关注和研究的东西。”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昊苏认为,阅读本书,不仅是回味小说中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体味作者是如何一步步虚构并建立一个世界,而它又是如何一步步被普罗大众与普通读者接受的。
探索哪吒形象“神魔”之变
2025年开年,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强势崛起,截至目前,该电影全球总票房突破146亿元,位列全球影史第七,更成为中国影史首部观影人次破3亿电影。不仅在数据上频频刷新纪录,经由电影的传播,一个经典的“魔童”哪吒形象也自此深深印刻在全球观众心中。哪吒为“魔”是天生如此还是艺术创造,在本书中,作者就此开设“单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解读。
陈洪表示,电影中的“魔童哪吒”形象,以及哪吒与敖丙“双胞胎”的情节核心是作者巧妙嫁接出的成果。“这种嫁接的近缘母本自然是《封神演义》,而若追寻基因谱系,则是自唐至明千年间,中外文化、雅俗文化交融所‘定型’的哪吒,虚与实、历史与文化的不断交织使得这一形象本身就带有潜在而又强烈的‘魔性’。”
记者了解到,哪吒从读音、形象到其概念的生成均与文化交融沟通密不可分。“哪吒在早期经文中其实是咒语里的一个发音。”陈洪表示,到唐朝时,一个名为“哪吒”的人格形象才从经文中确立出来,一直到晚唐,才有了关于哪吒的故事。宋朝时,哪吒的故事复杂起来了,其与父亲的关系,以及他“莲花化身”的身份也是在那时以传说的形式出现。于是在《封神演义》中,哪吒还骨肉给父母、莲花化身的故事便已然相当生动。“可以说,原著小说里的哪吒兼具善恶两性,善是主要的,但是也有恶作剧的一面,这是影片得以进行改编的基因。”
假如历史与小说均是“魔童”哪吒的嫁接母本,那么其“接穗”或许是来自于众多已然取得成功的小说、剧本,尤其是小说《绝代双骄》中的小“魔头”江小鱼。“魔童的设定,是把古龙武侠小说《绝代双骄》江小鱼与花无缺的部分情节,嫁接到哪吒与敖丙身上,促成了此次成功的改编。”陈洪表示,电影中哪吒的性格与命运与江小鱼等人物存在大量的相似因子,并进一步为类似形象注入了新的生命,这种“借势”在动画电影中取得了相当有意义的成功。
殷郊的“莎士比亚式”悲剧
从正义化身、帝师典范的姜子牙,到暴君代表、荒淫无道的商纣王,再到“妖女”苏妲己、散仙陆压、猛将黄飞虎,《封神演义》中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学形象,他们最终都破蛹化蝶,成为家喻户晓的角色。而在其中,近期得到广泛热议的殷郊同样具有深刻且复杂的文学性。据陈洪表示,殷郊的形象在《封神演义》里涉及的内容不太多,但在《封神演义》之前的《武王伐纣平话》中则承担了极为重要的戏份。
陈洪表示,在这本书中,殷郊被塑造成复仇者的形象,其父亲纣王因为宠幸妲己,残忍杀害了他的母亲,又听信妲己的话要杀他。若要给母亲报仇就要杀父亲,这就是一种伦理上的困境。而若要战胜父亲,则只能去投靠父母之邦的敌国,他要投降到敌人的阵营中,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正义。在进退与向背的犹豫和反复之间,不仅丧失了性命,还背负上了背信弃义的罪名。
“最后,在《武王伐纣平话》故事中,殷郊选择亲手杀死了纣王与妲己。”陈洪表示,这种内心的斗争和在矛盾面前的选择,很有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感觉,不是一般是非得失的问题,是内心的人格的挣扎。这种复杂的性格让人物变得丰满,也成为了小说中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形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