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需要实体书店?
《总有好书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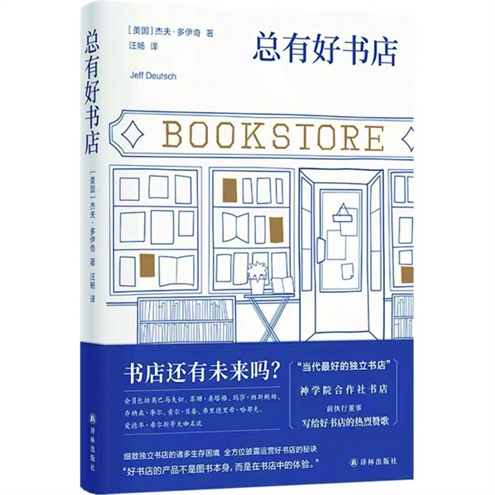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在一键购物时代,书店是否还有必要?当传统书籍式微,书店如何才能存活下去?日前,杰夫·多伊奇新书《总有好书店》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当代最好的独立书店”芝加哥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前执行董事,杰夫·多伊奇结合自己作为读者和书店经营者的经历,饱含激情地从空间、丰富性、价值、时间和社区等角度,展示了一家好书店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在他看来,在电子信息洪流的冲击下,好书店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实现其美好的愿景。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实习生 张渊栋
书店,如何从我们视野中缺席?
最早的书,是记载于竹木材料之上的简策。彼时,与王公富贾“积简充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庶民”对于文字与知识普遍的“视而不见”。随着印刷与造纸术的发明,书肆与名为“书”的新兴事物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汉代熙攘的集市上,于是“家贫无书”的王充,也能选择成为一名终日泡在洛阳书店中的“书虫”,自学成才并位列“后汉三贤”之一。两千多年时光淘洗中,总有一些“大隐于市”的安静场所敞开怀抱,接纳着那些求知若渴的读者,一家家书店的接续传承,让阅读成为了一项传承不息的文化事业。
然而,“如何定义一本书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的答案在现代社会逐渐变得不再清晰。如果说图书的出版与销售让知识得以首次摆脱垄断与独占,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则是在此基础上对知识的“二次分发”。假如人们可以面对屏幕完成更加高效而便捷的阅读,那些泛黄的纸张、文字的集合,那些一旦付梓便无法修改的句读排布,又能在多大意义上支撑着文明的演进呢?
不仅如此,从亚马逊再到当当、京东,图书交易逐渐成为了发生在光缆上不可见的数据交换与商业操作,线上图书商城以无限膨胀的虚拟体积压缩着现实世界中书店的店面面积,亿万级的大数据演算重构着每一个人的阅读志趣。原本的“读客”“书虫”,不得不同时成为一位寄居在数字世界的“网民”,孜孜不倦的“求知者”也逐渐成为信息爆炸这一社会图景下挑剔的“择知人”。新的阅读生态凭空出现,我们每个人却仿佛又一次成为了公元前的“庶民”,再次选择对书与书店“视而不见”。
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曾如此写道:“我们很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书店是一种悬置于‘濒临死亡的旧社会’ 和‘竭力诞生的新社会’之间的机构。”如此种种,当下实体书店的命运何在?
“当代最好的独立书店”如何做?
针对这一问题,杰夫·多伊奇在其新作《总有好书店》中以饱含深情的笔触与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书店何以在电子化浪潮中不仅存活,更能持续焕发活力的秘诀。
在书中,杰夫·多伊奇的核心论点直指书店本质:“好书店的产品不是图书本身,而是在书店中的体验。”事实上,芝加哥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转型经验同样成为这一论断的最佳注脚。记者了解到,这家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独立书店,曾因财务困境濒临倒闭。多伊奇接手后,通过“礼物经济”筹集资金维持着正常运营。所谓“礼物经济”,据他所说,是依靠会员捐赠与社区支持,而非单纯依赖图书销售的微薄利润,由此,书店的发展得以与其所在地和所在地的每个人息息相关。在这一策略的支持下,书店得以“起死回生”,更逐渐成为了“当代最好的独立书店”。
在对书店“空间”的剖析中,多伊奇进一步强调,书店的物理环境必须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与沉思。建筑师斯坦利·泰格曼为神学院合作社书店设计的新空间,刻意保留了老店“不完美”的特质:弯曲的过道、看似无序的书架布局,甚至“让顾客在书架间迷失方向”的设计理念,皆是为了复刻人类思想的漫游状态。书店因此成为一座思想的迷宫,读者在其中偶遇书籍的过程,恰似蒙田笔下“零碎片段”的散文,或是清少纳言《枕草子》中随性记录的生活琐思。
“书店首先要符合书店的本质,而非服务于简单的商品化和消费主义享乐,其次以空间和设计来激发会员的体验感,这种体验感并非是当代廉价的娱乐价值,而是‘摒弃’身体的思想漫游与交流。”杰夫·多伊奇表示,“让读者迷失方向”恰恰是空间构建的主题,以此,读者可以自由地去和知识与思想相遇,而非仅用双手拿起这一本或那一本书。书店的空间让读者成为“有灵感的”艺术家,而非抱有特定目的找寻一本书的匆匆旅客。
当下,书店应当成为什么?
当我们沉浸在书店中,浏览着茫茫多的图书时,我们会想些什么?在书中,多伊奇追溯着“浏览”这一词的词源,并认为其最初与“反刍”同义,暗含了沉思与消化之意。于是,当读者深入书店的每一排书架,浏览不仅是寻找书籍的过程,更是思想与书籍的互动仪式。作者将书店比作“一片牧场”,读者如反刍动物般在其中汲取养分,而书商的责任便是守护这片牧场的纯粹性——“拒绝日常生活的侵扰,创造一片只有书籍的天地”。
在这片“牧场”中生活的“反刍动物”可能多达十几种,多伊奇在书中详细列举着这些种类不同的“浏览者”类型:从徘徊的“漫游者”、观察细节的“矶鹬”,到寻求救赎的“忏悔者”,每一种类型都映射出读者与书籍关系的多样性。这种诗意化的描述,与亚马逊等电商平台的算法推荐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追求效率与精准,前者则推崇偶然性与深度思考的价值。正如《华盛顿邮报》书评人罗恩·查尔斯所言,这本书提供了“最动人的理由,证明书店的存在是必要的”。
而在多伊奇看来,好书店的蓬勃兴旺从不指望畅销作品,而是成千上万的单一“产品”。这些“产品”被耐心地放在书架上,等候着命中注定的读者前来翻阅。这一点构成了好书店的非凡与独特之处。当亚马逊等电商用算法精准投喂书单,当图书沦为电商的低价引流品,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却像一位固执的老派绅士,坚持用“低效”对抗这个时代。或许这家书店与光顾的读者都明白,这些低效之处绝不是对时间的挥霍,而是创建一家好书店至关重要的因素。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实习生 张渊栋
书店,如何从我们视野中缺席?
最早的书,是记载于竹木材料之上的简策。彼时,与王公富贾“积简充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庶民”对于文字与知识普遍的“视而不见”。随着印刷与造纸术的发明,书肆与名为“书”的新兴事物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汉代熙攘的集市上,于是“家贫无书”的王充,也能选择成为一名终日泡在洛阳书店中的“书虫”,自学成才并位列“后汉三贤”之一。两千多年时光淘洗中,总有一些“大隐于市”的安静场所敞开怀抱,接纳着那些求知若渴的读者,一家家书店的接续传承,让阅读成为了一项传承不息的文化事业。
然而,“如何定义一本书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的答案在现代社会逐渐变得不再清晰。如果说图书的出版与销售让知识得以首次摆脱垄断与独占,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则是在此基础上对知识的“二次分发”。假如人们可以面对屏幕完成更加高效而便捷的阅读,那些泛黄的纸张、文字的集合,那些一旦付梓便无法修改的句读排布,又能在多大意义上支撑着文明的演进呢?
不仅如此,从亚马逊再到当当、京东,图书交易逐渐成为了发生在光缆上不可见的数据交换与商业操作,线上图书商城以无限膨胀的虚拟体积压缩着现实世界中书店的店面面积,亿万级的大数据演算重构着每一个人的阅读志趣。原本的“读客”“书虫”,不得不同时成为一位寄居在数字世界的“网民”,孜孜不倦的“求知者”也逐渐成为信息爆炸这一社会图景下挑剔的“择知人”。新的阅读生态凭空出现,我们每个人却仿佛又一次成为了公元前的“庶民”,再次选择对书与书店“视而不见”。
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曾如此写道:“我们很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书店是一种悬置于‘濒临死亡的旧社会’ 和‘竭力诞生的新社会’之间的机构。”如此种种,当下实体书店的命运何在?
“当代最好的独立书店”如何做?
针对这一问题,杰夫·多伊奇在其新作《总有好书店》中以饱含深情的笔触与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书店何以在电子化浪潮中不仅存活,更能持续焕发活力的秘诀。
在书中,杰夫·多伊奇的核心论点直指书店本质:“好书店的产品不是图书本身,而是在书店中的体验。”事实上,芝加哥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转型经验同样成为这一论断的最佳注脚。记者了解到,这家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独立书店,曾因财务困境濒临倒闭。多伊奇接手后,通过“礼物经济”筹集资金维持着正常运营。所谓“礼物经济”,据他所说,是依靠会员捐赠与社区支持,而非单纯依赖图书销售的微薄利润,由此,书店的发展得以与其所在地和所在地的每个人息息相关。在这一策略的支持下,书店得以“起死回生”,更逐渐成为了“当代最好的独立书店”。
在对书店“空间”的剖析中,多伊奇进一步强调,书店的物理环境必须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与沉思。建筑师斯坦利·泰格曼为神学院合作社书店设计的新空间,刻意保留了老店“不完美”的特质:弯曲的过道、看似无序的书架布局,甚至“让顾客在书架间迷失方向”的设计理念,皆是为了复刻人类思想的漫游状态。书店因此成为一座思想的迷宫,读者在其中偶遇书籍的过程,恰似蒙田笔下“零碎片段”的散文,或是清少纳言《枕草子》中随性记录的生活琐思。
“书店首先要符合书店的本质,而非服务于简单的商品化和消费主义享乐,其次以空间和设计来激发会员的体验感,这种体验感并非是当代廉价的娱乐价值,而是‘摒弃’身体的思想漫游与交流。”杰夫·多伊奇表示,“让读者迷失方向”恰恰是空间构建的主题,以此,读者可以自由地去和知识与思想相遇,而非仅用双手拿起这一本或那一本书。书店的空间让读者成为“有灵感的”艺术家,而非抱有特定目的找寻一本书的匆匆旅客。
当下,书店应当成为什么?
当我们沉浸在书店中,浏览着茫茫多的图书时,我们会想些什么?在书中,多伊奇追溯着“浏览”这一词的词源,并认为其最初与“反刍”同义,暗含了沉思与消化之意。于是,当读者深入书店的每一排书架,浏览不仅是寻找书籍的过程,更是思想与书籍的互动仪式。作者将书店比作“一片牧场”,读者如反刍动物般在其中汲取养分,而书商的责任便是守护这片牧场的纯粹性——“拒绝日常生活的侵扰,创造一片只有书籍的天地”。
在这片“牧场”中生活的“反刍动物”可能多达十几种,多伊奇在书中详细列举着这些种类不同的“浏览者”类型:从徘徊的“漫游者”、观察细节的“矶鹬”,到寻求救赎的“忏悔者”,每一种类型都映射出读者与书籍关系的多样性。这种诗意化的描述,与亚马逊等电商平台的算法推荐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追求效率与精准,前者则推崇偶然性与深度思考的价值。正如《华盛顿邮报》书评人罗恩·查尔斯所言,这本书提供了“最动人的理由,证明书店的存在是必要的”。
而在多伊奇看来,好书店的蓬勃兴旺从不指望畅销作品,而是成千上万的单一“产品”。这些“产品”被耐心地放在书架上,等候着命中注定的读者前来翻阅。这一点构成了好书店的非凡与独特之处。当亚马逊等电商用算法精准投喂书单,当图书沦为电商的低价引流品,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却像一位固执的老派绅士,坚持用“低效”对抗这个时代。或许这家书店与光顾的读者都明白,这些低效之处绝不是对时间的挥霍,而是创建一家好书店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