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
——共同构筑的集体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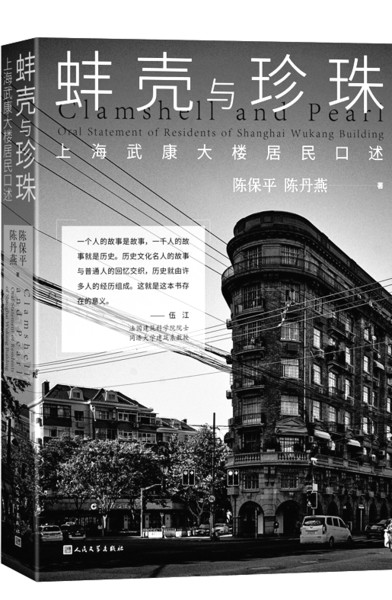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70年代末发还抄家物资的单子里,有张纸条上写,有一千多张自灌唱片“还不出”。我勿晓得灌唱片,只晓得我家录音器材相当多。早先爹爹会打开橱门,东一样西一样稀奇古怪的设备,弄给我看,讲给我听。可惜那时我不到十岁,听不大懂,就算当时勉强懂了,也记不牢。
印象深的是钢丝录音机,方方的,比我家常用的磁带盘式录音机小一点。我还帮爹爹理过钢丝录音盘。印象中,钢丝录音带,或者应该叫“丝”,假使全乱了,基本上理不好。
记得钢丝录音机,是因为爹爹一边弄,一边讲有趣的事。爹爹讲,他第一次看到钢丝录音机,是赵元任拿出来“显摆”。爹爹听力记忆相当好,就学给我听,赵元任录一段话,正过来放,再倒过来放。
爹爹还真的倒过来讲英文。小辰光耳朵灵,虽然不大懂英文,说不定反而客观。因为,脑子里没有习惯性的“正道”,当裁判思路不受干扰。反正就听有啥音,排列能不能对得起来。小人嘛,要是能捉到大人有错,用上海通俗说法:勿要太神气噢(很得意)。
岔开去讲个小插曲:我是先识五线谱后识字的,爹爹教我弹钢琴。实际上他就带我入门,让我自己学。不过我弹的辰光,爹爹不离开房间,要么编唱词跟我对唱,要么坐在旁边看书。有一次,爹爹眼睛盯在书上,一没看琴谱,二没看琴键,突然指出我弹错一个音。我哪能服气,强词夺理。姆妈在房间外面听了好笑,熬不牢跑进来,用上海话“请教”一对父女:哎,我倒听糊涂了,倷两个人,到底啥人教啥人啊?
再回到岔开去的前头,反正,假使句子短,正读反读对不对,还是听得出来的。大约摸听起来,爹爹没骗我。
那时候,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还只有蜡筒录音机。爹爹是语音室助教,帮刘半农忙。赵元任从国外带回来钢丝录音机,算是先进设备。赵元任让大家试,别的人文科出身,不敢碰“高级”机器。沈仲章考进北大是读物理的,就带头试,当场就会了,还蛮得意。后来接触的技术复杂了,回想起来实在是“小儿科”。
接下来,就讲帮人家录音。有时,专业机构的人作为项目采访民间音乐家,录了音带回去,一放声音不理想,或者漏了重要的人,漏了重要的曲目,就来寻沈仲章,能不能想办法补救。
印象深的是钢丝录音机,方方的,比我家常用的磁带盘式录音机小一点。我还帮爹爹理过钢丝录音盘。印象中,钢丝录音带,或者应该叫“丝”,假使全乱了,基本上理不好。
记得钢丝录音机,是因为爹爹一边弄,一边讲有趣的事。爹爹讲,他第一次看到钢丝录音机,是赵元任拿出来“显摆”。爹爹听力记忆相当好,就学给我听,赵元任录一段话,正过来放,再倒过来放。
爹爹还真的倒过来讲英文。小辰光耳朵灵,虽然不大懂英文,说不定反而客观。因为,脑子里没有习惯性的“正道”,当裁判思路不受干扰。反正就听有啥音,排列能不能对得起来。小人嘛,要是能捉到大人有错,用上海通俗说法:勿要太神气噢(很得意)。
岔开去讲个小插曲:我是先识五线谱后识字的,爹爹教我弹钢琴。实际上他就带我入门,让我自己学。不过我弹的辰光,爹爹不离开房间,要么编唱词跟我对唱,要么坐在旁边看书。有一次,爹爹眼睛盯在书上,一没看琴谱,二没看琴键,突然指出我弹错一个音。我哪能服气,强词夺理。姆妈在房间外面听了好笑,熬不牢跑进来,用上海话“请教”一对父女:哎,我倒听糊涂了,倷两个人,到底啥人教啥人啊?
再回到岔开去的前头,反正,假使句子短,正读反读对不对,还是听得出来的。大约摸听起来,爹爹没骗我。
那时候,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还只有蜡筒录音机。爹爹是语音室助教,帮刘半农忙。赵元任从国外带回来钢丝录音机,算是先进设备。赵元任让大家试,别的人文科出身,不敢碰“高级”机器。沈仲章考进北大是读物理的,就带头试,当场就会了,还蛮得意。后来接触的技术复杂了,回想起来实在是“小儿科”。
接下来,就讲帮人家录音。有时,专业机构的人作为项目采访民间音乐家,录了音带回去,一放声音不理想,或者漏了重要的人,漏了重要的曲目,就来寻沈仲章,能不能想办法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