呻吟声
——残酷而无意义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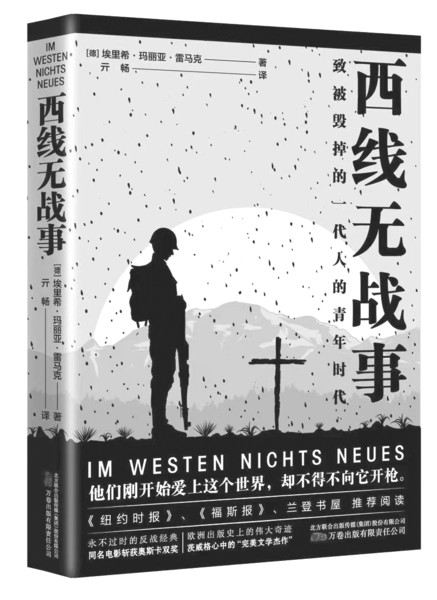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我坐了起来,突然觉得很孤单。有卡特在,真好。他若有所思地看向前线,说道:“如果不那么危险的话,这可以说是一场漂亮的烟火表演了。”
炮弹击中了我们的后方。几个新兵被吓了一跳。几分钟后又发生一次攻击,比前一次离我们更近。卡特敲了敲烟斗,“有重火力。”
猛攻已经开始了。我们匆忙地匍匐着爬走。下一次的攻击或许就会到我们这儿了。
几个人尖叫起来。地平线上蹿出了几颗绿色导弹。泥土飞扬,弹片呼啸而过,炮弹的撞击声消失后仍能听到四下里传来的不绝如缕的响声。
我们旁边躺着一个受惊的新兵,他有一头浅金色的头发,用手捂住脸,头盔已经掉了。我把头盔帮他找了回来,想重新给他戴上。他抬起头,一把推开头盔,像个孩子似的钻到我的胳膊下,紧贴着我的胸口,瘦削的肩膀止不住地颤抖着。凯梅里奇也有这样的肩膀。
我让他依偎在我怀里。为了让头盔至少有些用处,我把它放在了他的屁股上,这不是在胡闹,而是因为这个位置比较特殊—虽然肉厚,但被子弹射中的话就会疼得要命,得整月趴在病床上,就算好了,也很可能会变成瘸子。
不知道又有哪个地方受到重火力攻击,炮弹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喊叫。
现在终于安静了。炮火已经转移到对面的最后一个储备战壕。我们冒险朝那边看了一眼—红色的导弹在天空中飞舞,一场攻击或许即将到来。
我们这边仍然很平静。我坐起身来,摇了摇新兵的肩膀,“都过去了,孩子!我们都还活着。”
他惊慌失措地四下张望。我又对他说:“以后会习惯的。”
他现在注意到了自己的头盔,赶忙拿起来戴在头上,慢慢地回过神来。突然,他的脸色通红,看起来有些尴尬。他小心地用手摸了摸屁股,痛苦地看着我。我立刻就明白了:他得了炮弹热。其实,我并没有把头盔放在那个位置。我忙安慰他道:“这一点也不丢人; 不光是你,挺多人在第一次上战场后都拉裤子了。去把你的内裤扔掉。这不是什么大事—”
他不好意思地走了。周围依旧安静,但仍能听到呻吟声。“怎么回事,阿尔伯特?”我问。“那边有几个小队被击中了。”呻吟声还在继续。不是人的声音,人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卡特说:“是受伤的马。”
炮弹击中了我们的后方。几个新兵被吓了一跳。几分钟后又发生一次攻击,比前一次离我们更近。卡特敲了敲烟斗,“有重火力。”
猛攻已经开始了。我们匆忙地匍匐着爬走。下一次的攻击或许就会到我们这儿了。
几个人尖叫起来。地平线上蹿出了几颗绿色导弹。泥土飞扬,弹片呼啸而过,炮弹的撞击声消失后仍能听到四下里传来的不绝如缕的响声。
我们旁边躺着一个受惊的新兵,他有一头浅金色的头发,用手捂住脸,头盔已经掉了。我把头盔帮他找了回来,想重新给他戴上。他抬起头,一把推开头盔,像个孩子似的钻到我的胳膊下,紧贴着我的胸口,瘦削的肩膀止不住地颤抖着。凯梅里奇也有这样的肩膀。
我让他依偎在我怀里。为了让头盔至少有些用处,我把它放在了他的屁股上,这不是在胡闹,而是因为这个位置比较特殊—虽然肉厚,但被子弹射中的话就会疼得要命,得整月趴在病床上,就算好了,也很可能会变成瘸子。
不知道又有哪个地方受到重火力攻击,炮弹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喊叫。
现在终于安静了。炮火已经转移到对面的最后一个储备战壕。我们冒险朝那边看了一眼—红色的导弹在天空中飞舞,一场攻击或许即将到来。
我们这边仍然很平静。我坐起身来,摇了摇新兵的肩膀,“都过去了,孩子!我们都还活着。”
他惊慌失措地四下张望。我又对他说:“以后会习惯的。”
他现在注意到了自己的头盔,赶忙拿起来戴在头上,慢慢地回过神来。突然,他的脸色通红,看起来有些尴尬。他小心地用手摸了摸屁股,痛苦地看着我。我立刻就明白了:他得了炮弹热。其实,我并没有把头盔放在那个位置。我忙安慰他道:“这一点也不丢人; 不光是你,挺多人在第一次上战场后都拉裤子了。去把你的内裤扔掉。这不是什么大事—”
他不好意思地走了。周围依旧安静,但仍能听到呻吟声。“怎么回事,阿尔伯特?”我问。“那边有几个小队被击中了。”呻吟声还在继续。不是人的声音,人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卡特说:“是受伤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