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史家孔范今逝世 享年82岁
以人文情怀 观照百年文史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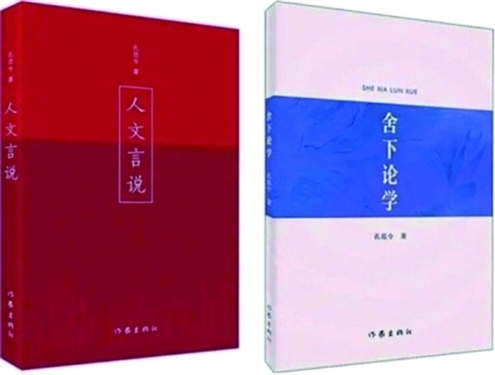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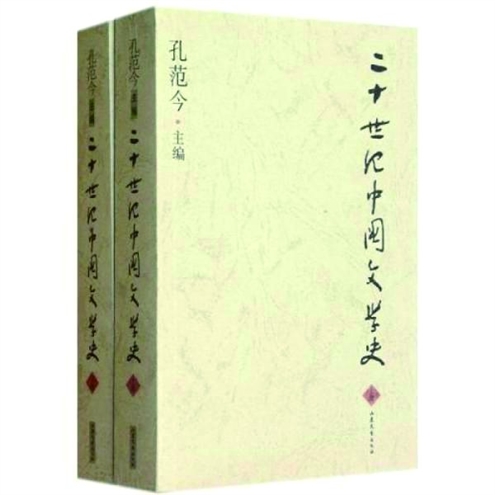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5月31日,山东大学文学院发布讣告:著名文学史家、杰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山东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孔范今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5月30日20时50分在济南逝世,享年82岁。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孔范今在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写作等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重要成就,其与人为善、心怀悲悯的人文精神与融理论探索、文学史建构和史料文献发掘为一体的学术实践,无不深切影响着后来者的文学之路。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朱德蒙 于洋
一位饱含人文情怀的学者
“我叫孔范今。”多年以后,一次久违的同学聚会上,1962级山大中文系学子的脑海中又一次浮现起这句夹杂着浓厚曲阜口音的普通话。而出现在眼前的却已不再是那个背着一小袋地瓜面漫步于山大校园中的青年学子,这位老人满头白发,只在眉眼间还隐约能看出年轻时的英俊与随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束人文精神之光在他身上愈发透亮,从孔子故里走入泉城济南,携数以百万的文字“穿梭”文学与历史之海,不变的,是孔范今执着一生的人文情怀与学术坚持。
据孔范今此前回忆,小时家境贫穷,只能想尽各种方式艰难求生。在这种窘境下,一碗掺了面粉的开水从一位同样深受饥饿折磨的妇人手里递出,送到自己手中。这件看似微小的事情,其中蕴含的人性中的善却给了孔范今一种极大的震撼,正如孔范今后来所言,于他来说,投身人文研究不仅是因为来自圣贤的教导,“还有生命中那些触动我的人文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孔范今的求学之路一发不可收拾,从“蹭课”到“蹭书”,无论遇到何种困境也不曾中断。这也最终使得孔范今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清华北大的理工学科,转而来到山东大学做起人文研究。
与人为善、心怀悲悯,作为孔范今做人治学的第一准则,不仅贯穿了其学术之路,也成为其人生旅程中最为重要的航标。此后,一位勇于探索、富于创建的杰出学者,一位胸襟坦荡、敢于担当的优秀学科带头人历经数十年如一日的苦心孤诣最终得以成就。与此同时,在这种强烈人文情怀的指引与感召下,中国百年文学史的“地图”得以补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山大学派”最终得以建立和发展。
一场文学史的“补天之路”
“直到退休前,我没有一天在晚上12点之前睡觉,也没有一天中午睡过午觉。”在一次采访中,孔范今曾坦言。对文学历史的考察与研究是尤为系统而全面的功课,直面历史,不仅是考察历史上精彩纷呈的事件与人物,还要从更为宏观与立体的视角上遍观各个面向,尽览诸多可能,这对于孔范今来说是真正值得其奉献一生的大事业。
“如何才能算是恢复到或者说把握住了对象及其意义存在的本真性”“为什么近百年内在文化、文学乃至学术观念的历史发展中,会数次发生自我否定性的反复回旋的现象”……这些问题频频困扰着年轻的孔范今。经过系统的研究,孔范今意识到,首要工作是将眼前“残缺不全”的现代文学世界尽可能“复原”完整,在当时,这是一条国内学术界“少有人走的路”。
这种被他形象地称为“知识考古”的艰难求索最终促成了一次为追寻文学作品跨越整个中国的学术苦旅,“有些连名目也不知道的,就要翻检旧时的报章杂志,从中发现线索,再按图索骥到各方寻找。”在一次采访中,孔范今表示,北到东北三省,南到福建、广东,当时自己带领着数人小团队奔波于全国各地。1990年,孔范今等人历经5年整理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出版,4卷14册、8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最终成为了文学史“大厦”的一块基石,极大刷新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固有认知。
此后,带着强烈的历史感,以丰沛而全面的文学资料为基础,孔范今又撰写多部著作,探讨亟待重建的新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观。1992年,孔范今出版的学术专著《悖论与选择》出版,其中孔范今倡导将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这种悖论性表现为这一时期历史的否定式发展的回旋图式,救亡与启蒙构成了20世纪悖论性历史结构和现代转型进程的两大支点。”此后,《走出历史的峡谷》《重构与对话》《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论》等一系列著作同样相继问世,历经30余年的积淀,孔范今以过于常人的精力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思考架构。
桃李不言,誉满学界
“我到他家单独求教不少于50次,印象中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总是一句话‘来吧,咱们聊聊’。”在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知遥看来,高深的学术造诣与亲切随和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作为孔范今弟子,马知遥在接受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与恩师初见时,自己已然参加工作数年。年轻时,马知遥经常参加济南市内各类文学活动,便总能见到孔范今。后来,被孔范今独到的文学理论折服倾倒之余,自己也升起了回到校园继续深造的念头。听说此事,孔范今没有任何犹豫:“只要愿意来读书,孔门为你敞开。”一句话开启的不仅仅是一条漫长的学术之路,还有一段深厚的师生之谊。
多年后,回望起这段经历,马知遥感慨万千,“后来我到天津深造并留校天津大学,每每到春节回去看他,他都很高兴,给人介绍,‘这是我的学生,是天津大学的教授’。”学术上的教导与生活上的支持,让自己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支持,恩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人为师的高洁品质,也影响着自己,成为了一种文脉的传承。
听闻孔范今逝世的消息,学界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与怀念。在唁电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认为范孔今“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与转型的中坚力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郑州大学文学院等亦纷纷表示,孔范今“是山东和全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参与者与引领者,”“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对后学提携关爱有加,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学人。”孔范今的人格魅力与治学精神深切地感染着众多同行者。
两年前,一本“不起眼”的小书《舍下论学》正式出版,与另一本小书《人文言说》一起,成为了孔范今留给人们最后的礼物。据了解,退休以后的孔范今仍然一刻不停地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回望自己一生的求索与探寻,孔范今时常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话想说”。可年逾古稀,已然身患眼疾,加之体力衰退,著书的愿望似乎就要成空。
得知此事后,几位几十年前聆听孔范今教诲的“老学生”结伴而来,以口述录音的方式将一段段珍贵的学术理论整理成文字,发布成书。在那些声音回荡的下午,默默陪伴在老师身旁的几位学子,不知是否会回想起几十年前坐在课堂里的自己,在一位精神焕发的老师教导下共同畅谈文学、纵论历史的时刻。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孔范今在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写作等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重要成就,其与人为善、心怀悲悯的人文精神与融理论探索、文学史建构和史料文献发掘为一体的学术实践,无不深切影响着后来者的文学之路。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朱德蒙 于洋
一位饱含人文情怀的学者
“我叫孔范今。”多年以后,一次久违的同学聚会上,1962级山大中文系学子的脑海中又一次浮现起这句夹杂着浓厚曲阜口音的普通话。而出现在眼前的却已不再是那个背着一小袋地瓜面漫步于山大校园中的青年学子,这位老人满头白发,只在眉眼间还隐约能看出年轻时的英俊与随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束人文精神之光在他身上愈发透亮,从孔子故里走入泉城济南,携数以百万的文字“穿梭”文学与历史之海,不变的,是孔范今执着一生的人文情怀与学术坚持。
据孔范今此前回忆,小时家境贫穷,只能想尽各种方式艰难求生。在这种窘境下,一碗掺了面粉的开水从一位同样深受饥饿折磨的妇人手里递出,送到自己手中。这件看似微小的事情,其中蕴含的人性中的善却给了孔范今一种极大的震撼,正如孔范今后来所言,于他来说,投身人文研究不仅是因为来自圣贤的教导,“还有生命中那些触动我的人文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孔范今的求学之路一发不可收拾,从“蹭课”到“蹭书”,无论遇到何种困境也不曾中断。这也最终使得孔范今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清华北大的理工学科,转而来到山东大学做起人文研究。
与人为善、心怀悲悯,作为孔范今做人治学的第一准则,不仅贯穿了其学术之路,也成为其人生旅程中最为重要的航标。此后,一位勇于探索、富于创建的杰出学者,一位胸襟坦荡、敢于担当的优秀学科带头人历经数十年如一日的苦心孤诣最终得以成就。与此同时,在这种强烈人文情怀的指引与感召下,中国百年文学史的“地图”得以补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山大学派”最终得以建立和发展。
一场文学史的“补天之路”
“直到退休前,我没有一天在晚上12点之前睡觉,也没有一天中午睡过午觉。”在一次采访中,孔范今曾坦言。对文学历史的考察与研究是尤为系统而全面的功课,直面历史,不仅是考察历史上精彩纷呈的事件与人物,还要从更为宏观与立体的视角上遍观各个面向,尽览诸多可能,这对于孔范今来说是真正值得其奉献一生的大事业。
“如何才能算是恢复到或者说把握住了对象及其意义存在的本真性”“为什么近百年内在文化、文学乃至学术观念的历史发展中,会数次发生自我否定性的反复回旋的现象”……这些问题频频困扰着年轻的孔范今。经过系统的研究,孔范今意识到,首要工作是将眼前“残缺不全”的现代文学世界尽可能“复原”完整,在当时,这是一条国内学术界“少有人走的路”。
这种被他形象地称为“知识考古”的艰难求索最终促成了一次为追寻文学作品跨越整个中国的学术苦旅,“有些连名目也不知道的,就要翻检旧时的报章杂志,从中发现线索,再按图索骥到各方寻找。”在一次采访中,孔范今表示,北到东北三省,南到福建、广东,当时自己带领着数人小团队奔波于全国各地。1990年,孔范今等人历经5年整理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出版,4卷14册、8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最终成为了文学史“大厦”的一块基石,极大刷新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固有认知。
此后,带着强烈的历史感,以丰沛而全面的文学资料为基础,孔范今又撰写多部著作,探讨亟待重建的新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观。1992年,孔范今出版的学术专著《悖论与选择》出版,其中孔范今倡导将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这种悖论性表现为这一时期历史的否定式发展的回旋图式,救亡与启蒙构成了20世纪悖论性历史结构和现代转型进程的两大支点。”此后,《走出历史的峡谷》《重构与对话》《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论》等一系列著作同样相继问世,历经30余年的积淀,孔范今以过于常人的精力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思考架构。
桃李不言,誉满学界
“我到他家单独求教不少于50次,印象中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总是一句话‘来吧,咱们聊聊’。”在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知遥看来,高深的学术造诣与亲切随和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作为孔范今弟子,马知遥在接受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与恩师初见时,自己已然参加工作数年。年轻时,马知遥经常参加济南市内各类文学活动,便总能见到孔范今。后来,被孔范今独到的文学理论折服倾倒之余,自己也升起了回到校园继续深造的念头。听说此事,孔范今没有任何犹豫:“只要愿意来读书,孔门为你敞开。”一句话开启的不仅仅是一条漫长的学术之路,还有一段深厚的师生之谊。
多年后,回望起这段经历,马知遥感慨万千,“后来我到天津深造并留校天津大学,每每到春节回去看他,他都很高兴,给人介绍,‘这是我的学生,是天津大学的教授’。”学术上的教导与生活上的支持,让自己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支持,恩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人为师的高洁品质,也影响着自己,成为了一种文脉的传承。
听闻孔范今逝世的消息,学界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与怀念。在唁电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认为范孔今“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与转型的中坚力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郑州大学文学院等亦纷纷表示,孔范今“是山东和全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参与者与引领者,”“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对后学提携关爱有加,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学人。”孔范今的人格魅力与治学精神深切地感染着众多同行者。
两年前,一本“不起眼”的小书《舍下论学》正式出版,与另一本小书《人文言说》一起,成为了孔范今留给人们最后的礼物。据了解,退休以后的孔范今仍然一刻不停地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回望自己一生的求索与探寻,孔范今时常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话想说”。可年逾古稀,已然身患眼疾,加之体力衰退,著书的愿望似乎就要成空。
得知此事后,几位几十年前聆听孔范今教诲的“老学生”结伴而来,以口述录音的方式将一段段珍贵的学术理论整理成文字,发布成书。在那些声音回荡的下午,默默陪伴在老师身旁的几位学子,不知是否会回想起几十年前坐在课堂里的自己,在一位精神焕发的老师教导下共同畅谈文学、纵论历史的时刻。